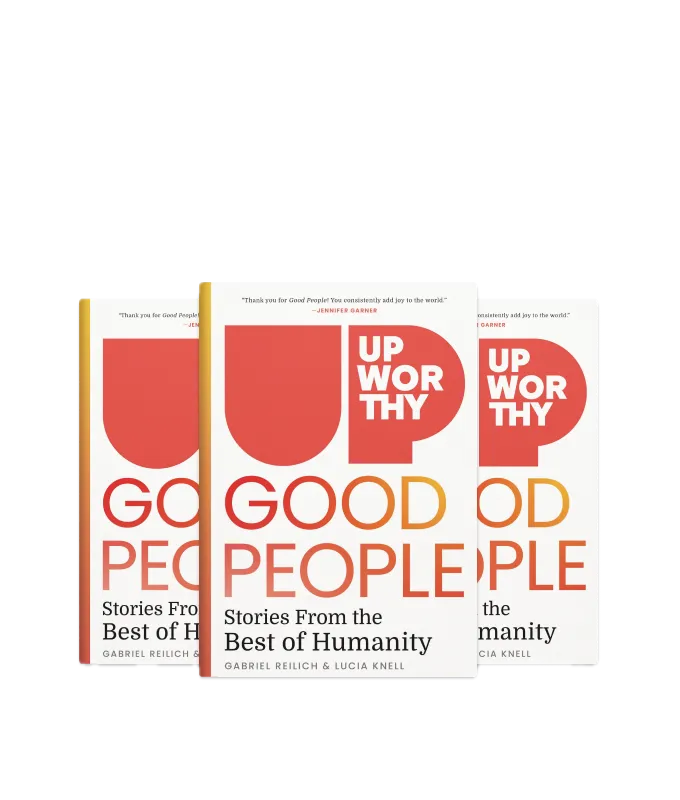如果你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我想喝啤酒(或其他酒精饮料)可能是你放松并忽视自己是个可怕的人这一事实的一种方式,这种人正在以鼠疫为自豪的速度阻碍人类进步。然而,对于一些自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人来说,在2019年6月的德国,一个周末并不那么轻松。根据《新闻周刊》报道,数百名聚集在奥斯特里茨参加“盾与剑音乐节”的新纳粹分子,在他们这个爱听糟糕音乐的仇恨集会中,被法院颁布的禁酒令弄得干巴巴不舒服。
禁令的目的是防止可能爆发的暴力(你知道它会的…),警方从参加这个持续一个周末的活动中的人们那里扣押了超过一千加仑的酒。他们甚至在推特上发布了没收酒精的照片。但是,这只是一半的故事。已经不得不忍受这些仇恨者的奥斯特里茨镇居民(他们在去年希特勒生日那天举办了同样的音乐节)知道,这样的禁令不会阻止节日参与者在城里试图获得更多的酒。
因此,居民们在节日前一周聚在一起,制定了一个能真正让白人至上主义者意识到新纳粹音乐有多糟糕的计划:他们买下了整个镇的啤酒供应。“我们想让纳粹干杯无酒可喝,”当地活动家乔治·萨迪特告诉记者。“我们认为,如果有一个禁酒令即将到来,我们就去Penny [超市]把货架清空。”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从奥斯特里茨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这里有不容忍这一切的人,并表示‘我们这里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树立榜样……’”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当地女性告诉ZDF电视台说。同时,居民们还在节日期间举行了两次反抗议活动,并举办了一个“和平节”,以明确表示不欢迎偏执态度。如果明年同样的音乐节再次在这个镇上举行,购票者应该意识到奥斯特里茨说白人至上主义者不受欢迎时是不含糊的。
同时也有一些好消息:除了居民们毫不畏惧地传达他们不容忍不宽容的信息外,极右翼音乐节的出席人数在过去一年急剧减少。根据BBC报道,2018年有1,200人参加,而今年呢?大约500-600人。希望明年节日不要再上演。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2019年6月24日
从外面看,我有一个完美的童年。我住在一个有四个卧室的房子里,有一只狗和一个围起来的后院。
我穿着百货商店的衣服和Stride Rite的鞋子,有最新最好的衣服和玩具。从芭比娃娃到卷心菜娃娃,从任天堂、超任、Gameboy到SEGA Genesis,我都有。我还有一对充满爱的父母。我的父母参加了我在学校的所有制作和戏剧。他们从不缺席任何一个荣誉午宴,并看着我拿到所有的出勤奖。但在背后,事情是不同的。它们是不同的,我的母亲如恶梦一般。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精神上、情感上和言语上虐待我。
当然,我不知道这件事。至少最初不知道。直到伤害已经造成,但那是因为——就像大多数虐待者一样——她的虐待开始于操控。她爱我,娇惯我,紧紧抱着我。她会说类似“妈妈爱你。妈妈需要你。你不想妈妈伤心,对吧?做这个我就会开心”的话。她让我相信我无法信任任何人。我的童年充满了沉默、羞耻和秘密。她把我与朋友分开。她告诉我不可以出去玩或有玩伴。永远不允许我有朋友过来,然后她开始贬低我。我不好。我笨。我是个“失望”
和“失败者”。事情变得更糟。在我十二岁生日到十三岁之间的某个时候,叫喊开始了。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因噪音和恐惧而震动。到我十四岁生日,我母亲的辱骂中夹杂着脏话。有时她试图打我或把我按住,因为我从小就被操控,我感到无助。我害怕、孤立、抑郁和孤独。我生活在恐惧中。我在我的“监狱”,即我的家中如履薄冰。好消息是,我最终逃出来了。当我高中毕业时,我把自己和我那微薄的行李移到了100英里之外,跨过两个州。
但伤害已经造成。在36岁的时候,我仍然在自信上挣扎。信任是个问题,我对批评的反应——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暗示的——都是个问题,我几乎没有朋友。但我的虐待童年也教会了我很多关于育儿的东西。我知道我的孩子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应得什么,为此我感到感激。我认为自己是#被保佑的。不要误会: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和扭曲,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它同时也完全符合逻辑,因为我破碎和被忽视的童年塑造了一个深爱且全心全意爱孩子的母亲。我把我的心写在我的袖子上。我给我的孩子他们最需要的东西:我的时间、倾听、耐心和支持。我的破碎童年教会我通过经验来引导。比如,我因信任被背叛(以及因为我被告知不要让别人接近)而有信任问题,所以我在我的孩子周围时,总是刻意推自己的界限。
因为我希望他们看到我没有看到的东西。我希望他们能够依赖他人以一种我从未能做到的方式。而我的破碎童年教会我不应该说什么。我很少使用“不能”或“不”。我经常表扬我的女儿。我专注于她的成就而非她的失败或缺点,当她“发作”或犯错误时,我谨慎选择我的话。我将她的感情与她的行为分开,让她能够理解:“生气没有关系。我也会感到沮丧。但发怒不是处理情感的健康方式。”我也告诉她我的感受。为什么?
因为成长过程中,我被告知的事情是“停止哭泣”和“冷静下来”,这些指令不只是让我感到痛苦和焦虑,它们还阻止我处理自己的情感。我仍然挣扎于说出更多的话,除了“我很好”或“我还好”。所以,尽管我对于自己在一个疏远的家庭、一个忽视的家庭、一个情感和言语虐待的家庭中长大感到不快,但我还是很高兴我的女儿不会,因为我的经历让我了解了我的孩子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我的经验教会了我如何以及为何需要打破这个循环。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2020年9月4日